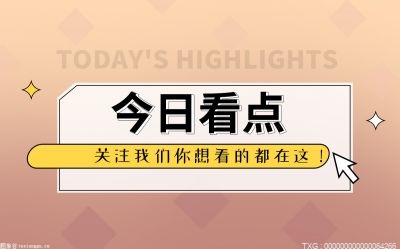独角戏与一群戏剧人的突围
聚光灯下,演员李腾飞脸上身上的汗滴清晰可见,呼吸尚未调匀的他,将观众送上的鲜花抛掷给热情的观众,表达感谢。
2023年1月2日下午,鼓楼西剧场独角戏《一只猿的报告》第三轮演出告一段落。所有的百感交集,都化在了斟满的热红酒和结实的拥抱里。
因为新冠疫情和防控政策,这轮演出从原定时间2022年国庆至今日终于完成,经历了至少三次延期。而在2022年漫长的三百多天里,民营剧场鼓楼西也从《一只猿的报告》获得的热烈反响,生发出《象棋的故事》《吉他男》等多部独角戏和相关的戏剧节策划。一个人的倾力演出,小团队的精心打磨,令这群戏剧人在特殊时期探索出一条“别样出路”;而创作伙伴们的灵感火花四溅,以及彼此间关系的升华,对戏剧艺术的深度理解,则成为他们在困境里的“意外”收获和治愈自身的力量。
 【资料图】
【资料图】
成为“一只猿”
开场音乐渐弱,近乎黝黑一片里,一个身穿大号西装、别着红领结的男人弓着背,踮着脚,踱步上台。
在之后的几十分钟里,“做报告者”的身份贯穿始终,但他却极少“安分”:斜肩、跺脚、瞪眼,吃虱子,扭屁股,要么一只手臂高高扬起,或从翻滚、咆哮迅疾地回到半蹲姿势,惊恐、好奇、驯服的眼神,交替流露。
哦,这原来是一只被囚禁的猿猴红彼得历经千辛万苦,通过模仿与“学习”,成为人类的过程。
▲《一只猿的报告》里,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进化之路”场景 图/塔苏
有观众形容,《一只猿的报告》主演李腾飞是在用骨骼表演。“看上去,他的骨骼完全弯成了猿猴的形态:脊柱前弯,股骨后翘,上肢长于下肢,行走为臂行。我能听到他骨关节的响动。加之他声音上的功力——逼真的猿啼,脸部肌肉的训练——野性的抽搐,说实话,我已经无法分辨他是人是猿。”
李腾飞个头不高,肌肉健硕,不是舞蹈表演者中常见的瘦高体形,但从舞台上的各种腾挪、空翻、大开大合的动作到戛然停住,可见其稳定性和柔韧性。“他是我认识的国内身体条件极好也最爱惜和善于挖掘身体的演员。”导演郗望不吝赞美。
“你从小便意识到自己身体条件的优势吗?”我问李腾飞。
“谈不上优势吧,我只是特别喜欢利用自己的身体来表达,表达一些语言之外的诗意。”
在《一只猿的报告》里,无论是红彼得回忆自己可能掉入海水中的游泳姿态,还是在舞台光束下、展现出的一只猿如何从爬行、半蹲,进化到直立行走的人,都呈现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诗意”。
童年时的李腾飞便向往空气丰沛,生灵繁茂的地方。之后,他又在工作坊里习得了如何捕捉动物身上,乃至风、火、气、黏土等物质中蕴藏的气质、神韵。
为了参透猿猴的姿态,他去了十多次北京动物园。隔着玻璃,他和它们一起抬头,努嘴,左右摇摆身体。只是,猩猩和游客已经没有太多互动了。“它们生下来就被观察。每天只有下午3点吃饭,那之前半小时是最激动的。会看看厨房有没有吃的,有没有人备菜。”
或许因为他去得太频繁,有一只叫思思的母猩猩,引起了他的注意,而他也引起了思思的注意。“它老趴在玻璃上看人,看小孩儿怎么吃东西,看大人怎么照顾小孩儿。就感觉它对外面人类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嫉妒似的,还有些忧郁。它可能意识不到自己一辈子只能待在这里。”
到底是谁看谁呢?李腾飞觉得,其实我们身边的“猩猩”还挺多的。这部戏的主题,也跟现实里人的境遇有多种层面上的相似。而“Listen to your inner ape(倾听你内心的猿)”,正是这部戏剧的英文名。
▲2022年12月28日, (左起) 李腾飞、郗望与鼓楼西戏剧制作人韩莉在 《一只猿的报告》 演出结束后跟观众交流 图/山羊
“寻找出路”
《一只猿的报告》改编自卡夫卡的短篇《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一战”期间,敏感的卡夫卡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人类的未来迈向不可逆转的泥淖。他用文字揭示出人类逐渐异化的处境,和从迷茫,恐惧转向绝望的心境。
在郗望看来,原作和他想表达的核心是驯化与规训。“为了进入另一个阶层或者另一个文明里,你要自我驯化,自我阉割。”
剧中,红彼得为了摆脱被拘禁的处境,意识到自己不能困在“猿”的身份里。他学会了向人类微笑,握手,学会了啐唾沫,学会了抽烟,学会了最为厌恶、但人类却乐于调教他的喝酒……
当他终于掌握了开启瓶盖、扔掉酒瓶,颤颤巍巍地说出第一句人话:“你好——”全剧的转折点由此而生。身为观众,那一刻的悲凉、纠缠,也随着红彼得的大声呼喊,翻来滚去。
对于“重生为人”的新世界,红彼得究竟是泰然处之,还是纠结、甚而嫌恶,心有悔痛?
排练之初,郗望没和李腾飞深入聊这个话题。“聊太多没用。经历了整个(排练)这么一遭再说。”
这让李腾飞有点发蒙。看了卡夫卡写的番外篇《红彼得》,有了些感觉。作品中记者去酒店采访巡演大获成功的红彼得,看到屋子里窗帘拉上,满地水果,红彼得躺在沙发上,意兴阑珊。“他的状态一直不太好,就靠着吃大量的水果想忘掉这一切。这种感觉,是不是和很多咱们所谓‘名人’的‘万众中的孤独’很像?你好似得到了一切,却对这个自己很拧巴。”
9月底联排时,我问起郗望,“规训之后的红彼得,究竟是意识到了成人的代价,还是已经不去反思了?”
“应该是两者之间吧。”他回答,“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一生是个悲剧。红彼得说道,我不要自由,只要出路。那种笼子里可以自在吃虱子的‘自由’,其实就是‘自欺欺人’吧,因为外部世界太差劲,你总得让自己合理化,才能活下去。”
整场戏的高潮,是后半部红彼得长达七八分钟的“控诉式”独白,这一长段仿写《自我控诉》的台词,出自排练中后期两人的二度创作。那时排演进入一段瓶颈期,李腾飞想起彼得·汉德克的《自我控诉》,忽然就在排练厅里读了起来,边读边把红彼得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掉,只剩裤衩,其他人看傻了,连声叫好。“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之前觉得这些文字很理性客观,当我们把红彼得代入进去,代入自己,就觉得更实在。虽然那些词看似无序、重叠,但有一股神奇的力量。”
郗望也对《自我控诉》有过阅读和心理准备。但他觉得,不能把原著完全“拿来”,必须要加入自己的话和融入当下的社会情态。于是两人分别写了一些文字,由导演汇总修改而成:
……
我走出了大自然
我变了
我变得都不自然了
我看到了你们的目光
我从你们的目光中看到自己
我学会了应该遵守规则
我学会了规则和规则里的例外
我融入了人类社会
但我变得独来独往了
我想去哪儿
回到曾经的那个铁笼子的木板前?
它的后面是森林么?
创作者对于红彼得“出路”的态度,从这些词句里,也可一窥端倪了。
▲《一只猿的报告》主创在2022年年末鼓楼西剧场第三轮演出后与观众合影 图/马向龙
挑战
戏剧大师彼得·布鲁克曾说:一个人穿过舞台就形成了戏剧。然而真正的独角戏,完全依靠一个人的语言与动作,实现情境和角色(甚至多个角色)的表达,无疑是对创作者的巨大考验。
在国内,提到“独角戏”,人们想到的要么是《夜奔》《思凡》这样古老的戏曲曲目,或是上世纪80年代游本昌、王景愚、王德顺这样的哑剧独角戏三杰,抑或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人的莎士比亚》这样的国外剧目,当代中国戏剧领域对独角戏的研究和实践还不算多见。
“独角戏可能都不太算一个单独的剧种吧?我没有特地钻研,不能妄言。”说到这个话题,《吉他男》的导演兼主演何雨繁笑道。“但我感觉,其实它的表演和创作规律和其他戏都一样,只不过有很大的限制条件。”
在鼓楼西这次的三部独角戏里,《一只猿的报告》和《吉他男》都是透过主角的独白来表现主题,唯有《象棋的故事》是一人分饰多角:B博士的紧绷,“棋王”的木讷,看客的松弛与犀利,如何在其间自如转换,对主演的业务水准颇有挑战。
故事讲的是一艘远洋客轮上,以“天才”著称的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琴多维奇出乎意料地被人群中的一位神秘乘客B博士战胜;闪回到B博士的回忆,原来他曾被纳粹单独囚禁在酒店数年,一本棋谱救赎了黑暗中的他,却也禁锢和扭曲了他的精神世界。
主创郭笑想摆脱他认为的“窠臼”表演,最后采用了“说书人”之法,两个主要人物和叙述者三角“跳进跳出”;加上他的戏曲身法、贯口、古诗词、哲学、音乐知识,几十年对传统文化的吸收,在这个舞台上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剧评人李静称之为“一个人的交响乐,一个人的万马千军,一个人的中西合璧,一个人的庄谐并举苦中作乐笑中带泪,一个人的理性与癫狂、蜂蜜与胆汁、囚禁与翻越”。
不过,两万字的台词中,大段的诗词背诵是否有炫技之嫌?人性受到禁锢后的压抑这一主题,会不会因此而被冲淡?在观众和评论者中也引发了争议。独角戏的创作者,如何能不被个人汩汩而出的才华捆绑,更恰当地服务于作品,或许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遇到不是以思想深度见长,情节又偏弱的剧作,独角戏演员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
何雨繁主演的《吉他男》改编自挪威剧作家约恩·福瑟的同名作,讲述一个失意的吉他手,在地铁和大街上宣泄人生的种种愁忿,质疑自己坚持的意义,质疑一切。一个多小时的台词和歌唱充满了语意的反复,从头到尾如一个人的喃喃呓语。
怎么样处理如此诗性的文本,如何通过表演和其他的方式做到“形散而神不散”,何雨繁没少发愁。他坦言,《吉他男》其实更适合在酒吧、吧台等很小的空间里来演出。能装200人的鼓楼西,对于这个戏反而尺度过大了。
“必须要用能量去抓住观众。”他用六根长长的彩带代指琴弦,寓意吉他男心中的艺术梦,在舞台上缠绕身体,配合色彩和亮度参差的灯光,营造出一种特别的讲述情境。如同读者对福瑟的态度,《吉他男》的观众也一样有“两极”的反应:要么喜欢,要么不能接受,这也在主创的预料之中。
▲《吉他男》 图/蔡园
已经演出了三轮的《一只猿的报告》,争执与磨合同样贯穿始终。
对李腾飞的肢体表现,郗望毫不担心。“最开始他在场上特别花哨,像C罗,我得琢磨怎么把他变成齐达内。”到后来,他反复调拨的是,如何利用而非滥用身体条件,更符合表演的需要。“我和腾飞经常讨论,我希望他明白的,是那些动作是否只是一只普通猩猩,还是来自红彼得,以及演员是否在角色上赋予了过多自我的性格。”
“比如,红彼得说,我学的第一件事是握手。这里腾飞下来和观众互动握手,他忍不住会笑。可是猩猩不会这么笑。这是李腾飞作为一个演员,他在意观众的认可。这一刻他不是猩猩了,而有些讨好观众,会把他对观众的期待袒露出来。”郗望解释。
排到一定程度,演员会陷入疲惫,甚至“皮了”。郗望不时地“点醒”李腾飞:“我看不到你的乐趣,你不要当演员了好吗?!”
忠言逆耳。李腾飞也只有在“棒喝”中停下来思考,为什么自己还要做这个事情。“他让我打开自己,比如面对观众该怎么放松自己,怎么激发出原始的表达欲。我也得在自己和本子周旋的时候,找到这样的乐趣。没有别人能帮你。”
因为独角戏,服化造型李金津和灯光师董火亮才与鼓楼西结缘。此前他们都有在分工明确的大剧组工作的经验。那样的团队阶梯分明,也因为专业隔层,而有一道道无形的墙。但在独角戏的排练里,大家可以很自由地表达,主创之间也毫无芥蒂。
李金津说自己属于交感神经比较旺盛,一进入工作,碰到有意思的戏,会兴奋得睡不着觉。“这次的导演会问起我,你对于某个段落怎么看,以前我很少会被问到这样看似‘超纲’的问题。但这回的创作者非常欢迎跨部门的意见,这也给我很大的鼓舞。”
《一只猿的报告》在排练厅联排阶段,董火亮对于“进化之路”的光并没有多敏感,当李腾飞到舞台上排练时,他突然发现,红彼得走出了那样一条从猿变成人又变成猿的纵深之路。“我喊停了一下,废掉了一支侧光灯,把它切成了一条光路的形状,效果呈现出来后大家都很兴奋。那不只是好看,更是有意味、有感情的。而且那条路从平面关系上看,不是特别均匀,而是越往前越窄、越往前越亮,像彗星一样。观众看了之后也有很多的反馈。”
“还有被关在笼子里的红彼得,底幕上投出的影子,并不是实心的光,而是剪刀拉开的不规则黑区。这个是我们几个到现场,突发奇想,在垃圾桶里找到可乐瓶,剪出随机的形状。”董火亮兴奋地回忆着,“包括我们会根据演出空间的不同,对灯光设计不断地调整和摒弃,也会保持很久的感情和热情。”但在比较大的群演制作里,不同演出地的灯光调整会非常谨慎,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在董火亮看来,这也是小剧场和独角戏的魅力所在。
回溯与圆梦
与“猿”的编创不同,郭笑与何雨繁这回都是同时身兼导演和主演双重身份。既多能,却也缺少了及时从客体角度来审视、调整表演的可能。
“独角戏”,越发显出它的孤独。
好的合作者可遇而不可求。说起来,这几部戏的出炉,原本就各有各的机缘,排演过程,也如同主创们对过往经历的回溯。
2011年李腾飞大学毕业来到北京,第一份工作是报社的夜班美编。白天他时间机动,除了看戏,几乎所有的空余时间都花在了各类表演工作坊。看人家在舞台上演戏,觉得自己努把力,也能站上去。直到出演鼓楼西剧场版《雷雨》中的鲁大海,领导和同事才了然这个老请假的美编还有如此才艺。
他离了职,失去经济来源,去各种剧团跑演出,一场可能也就分个几百块。“还是想干这个,念念不忘。”
郗望的戏剧教育完全来自在法国的那些年。他说到法国的第一周,自己的戏剧观就被颠覆了。老师要求学生们建立一个等候室的情境,不说话,就在情境里生活。“我像一个乡村画师,突然穿越到文艺复兴时期。在一间印象派画室,我发现那些画作活了,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就是这种感受。”
回国后,他在执行导演和表演指导的位置上从事创排辅助工作,可是,“带演员做工作坊,弄出一个小汇报给导演看”,并不是他心里真正的创作。
国内一些戏剧近年过于注重舞美灯光、虚浮的大场面制作,在他看来是本末倒置。“比如立了项以后,先定景儿,演员再去适应这个景和舞美。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戏剧当然要以舞台表演为核心,还有,文艺作品能不能诚实地说生活?”
一晃三十而立,两个认识了十年、却很少深度合作的年轻人,不谋而合。2020年,李腾飞与鼓楼西剧场签约,成为剧场签约演员之一。当去年年初,李腾飞读到卡夫卡的《致某科学院的报告》,又看了国外同行的演出视频,他俩心里的念头“噌”地窜出——就是它了。
“这是我想寻找的出路,做演员太被动了,不是勤不勤奋的问题,演员很难遇到自己喜欢的剧本,遇到了,像我这样的演员也演不上最理想的角色。”李腾飞说。
对郭笑,《象棋的故事》则是一个悬在脑海里二十余年后终于圆梦的结果。
30岁那年,郭笑在整理父亲的书时,翻到了一本1980年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斯蒂芬·茨威格小说四篇》,最后一篇《象棋的故事》读罢,他不忍释卷。“怎么还有B博士这样的人?法西斯竟用这种非常的手段?如果是我,可能半天(在里头)都待不住,我什么都招了。”郭笑既叹服于人物的韧性,也开始痴迷于象棋的魔力。他四处讨教,苦苦钻研,还特地拜访了谢思明等一众象棋大师。
“象棋”成了他的精神寄托,也是他半生文学梦的外化。“我愿意把生命浪费在这些美好的事情上。”但或许正因带着强烈的个人领悟,他很难再去和其他的导演、编剧、演员切磋交流这个作品,时间上也来不及,最后只剩下形单影只。
《象棋的故事》 图/李晏
在鼓楼西的食堂,月亮下的大门边,郭笑不止一次地和我慨叹,“80年代那会儿读书的人啊,我们通信的笔友、文友,周末把自行车一蹬,去香山,拿出本儿或者一叠纸,比比谁的诗好,谁写的文章强……可惜现在不是文学的时代,也不是戏剧时代,是短视频的时代。”
何雨繁如今是鼓楼西演员队长,他是《婚姻情境》里的约翰,也是《枕头人》里的警官图波斯基。曾经在清华戏剧队接受的锻造,成为他戏剧生涯里重要的一笔。那时中戏的老师徐平给剧社成员讲台词;1998年赖声川到北京排《红色的天空》,和演员林连昆也去剧社做过讲座。“当时话剧队的气氛很好,大家都是谈业务谈得多。读剧本、看录像,积极性很高。”
2005到2006年间,何雨繁参加了二三十个工作坊。虽然时移世易,但戏剧热情的消退,在他身上还没有出现。“只是,现在很难看到很成气候的戏剧力量。”
火苗
未曾料到,这气候正在渐渐浮起。
2022年3月的北京,雪一点点消融,李腾飞开始排练。那时没有谁会想到这只“猿”会成为行业现象。上半年疫情封控,郗望甚至报名去上了一个月的瑜伽教培课,作为职业的退路。
疫情之下,有的演员开滴滴、送外卖,李腾飞始终没迈出“体验生活”和转行谋生的那一步。“有戏就一直在工作。没有戏就焦虑没有戏。很少有演员能悠然自得吧。”但他自觉社交能力不强,也是个问题。“郗望说我不是那么游刃有余。”
到夏秋,形势起起落落,有了变化。再到冬天,几部独角戏分别在鼓楼西和其他城市上演,桂林、上海、阿那亚等地的邀约纷纷发来,观众的反馈一浪接一浪。
因为不牵涉太多创作者和资源,排练和演出都相对好控制,独角戏无意中成了2022年鼓楼西和行业里的一个喘息出口。
“独角戏有独特的优势,它可以轻装上阵,到很多城市去巡演,还能控制运营成本。”鼓楼西剧场创始人李羊朵说。夏秋之际,剧场顺势推出了汇集这三部作品的“独角show”,引发业内关注和讨论。一时间,许多演员纷纷表示也想演独角戏。剧场于是发起了“鼓楼西独角戏剧节”,面向全社会征集独角戏剧目。
鼓楼西副总李国杰介绍,他们在11月前后收到上百个录制了演出视频的作品,原本选取了其中的部分作为竞赛和展示剧目,还设置了观众投票和专家点评环节,后来因为疫情发展又临时取消,但这股势头仍然让他们欣喜。“这些作品里有对情感的讨论,有传统文化和话剧的结合。很有创造力。”
此前郗望从不觉得自己是戏剧圈的人。《一只猿的报告》面世,他学会了如何与观众和媒体沟通,如何正视和确立作为导演的社会身份,这是他这一年最大的收获。“在专业范围内,我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但怎么样跟方方面面打交道,明确我这个职业的社会属性,合理地分配资源、处理人际关系,这是我学习到的地方。”
最近这些日子,董火亮频繁地听到大家说,独角戏的曙光到来了。“先不说一个戏剧门类的活跃与当下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重要的是,当这束光出现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追上这束光,有没有足够多的创作者和热情推动,让小火苗点成一团篝火,可以更深地更稳固地扎在这片土地上。”
诚然,掘出第一捧水的时候,人们不知道它会不会变成一口井。但它的味道与担水人的付出,总会被品觉到。
2022年12月29日那夜的演出,当台上的红彼得酝酿良久,发出惊天地的一声“你好”,继而再次向观众挥手,李腾飞看到,台下有好些观众,也举起手来,浅浅地跟他道“你好——”。
“那给了我极大的力量。我感觉和观众建立了联系,他们对这只素昧平生的猩猩,开始共情了。最后红彼得结束了‘控诉’,结束了报告,和全场对视的时刻,我看着观众,感觉全场看进去了,他们脸上微妙的表情,就像我现在看着你,我能观察到,你在想什么。我能看到你们所有人的想法,我知道你们也在想要知道我要说什么,做什么,那是我最在意的。”
(参考资料:《李腾飞:如何成为一只猿》,《从“孤独”迈向“独到”才是独角戏的精彩》,《“一只猿”的细腻表演与民营剧团复苏》,《两个戏剧人的“出路”》,《谢幕报告001》,《讲故事的人,故事里的人》)
下一篇:最后一页
X 关闭